再續濫竽充數 – 第五輯 燈下之絮語
再續濫竽充數 – 第五輯 燈下之絮語
新北市(原台北縣)藝術家聯展茶會上,又一次“濫竽充數”的故事意外的發生了。我說的濫竽充數,是指即使有人給我機緣,凡是不夠資格的,我統統叫做濫竽充數。
幅員廣闊的新北市,擁有400萬人口和豐沛的人文底蘊。一年一度的藝術家聯展,每年都在春暖花開之際舉辦。市府團隊親自當藝文推手,設置展場和茶會,邀請了470位根鬚深厚的藝術家,參展年齡跨越老中青,最長者竟有96歲高齡,每人送一件創意作品。大家共聚一堂,以互相學習,互相觀摩的心態前來參展。展出作品有書法、水墨、油畫、雕塑、攝影、版畫等等,分別在8個行政區的8處展館同步展出,讓藝術種籽遍地開花。
2013年3月23日這一天,新北市的藝文大廳坐滿了老中青藝術家,開幕茶會上,有樂隊演奏,新北市市長朱立倫還親臨展場祝賀,並很親民地與到會所有藝術家一一握手。會後除了品嚐精美的點心外,民眾還可近距離與當地藝術家面對面交流。雖然我與藝術家的技藝相差十萬八千里,但在華人藝術家廖天照大師的強力推薦下,寧願他自己不參展,也硬要把我這個半路出家的素人作品(指非專業)給硬塞進去。實實在在讓我又做了一次“濫竽充數”。
這使我想起了台灣著名藝術家朱銘的第一次參展故事:那是在朱銘剛剛出徒不久,無名無份時,他的師父楊鳳英頂著自己的大名填表申請,卻故意在展出前兩天,謊說自己作品拿不出來,硬是把機會讓給了愛徒朱銘。館長起初只給5天展出時間,沒想到最後改為一個月,
又展了一年而名聲大噪。這正如席勒所說:“機會像一塊粗糙的石頭,只有在雕刻家的手中,才能獲得新生”。
此次展覽,我從居家大廳砌滿漂流木的作品中,選出高約55公分,用台灣香樟雕刻的“林來瘋”(林書豪)作品。那天玻璃櫃中,眾多男性雕刻家的大作中,只有我一個小女人的素人作品與大作並列一起,實在有些汗顏,感覺就像萬綠叢中一個“疤”一樣的獻醜。但能站在藝術前輩中,體驗平凡而深刻的藝術觀摩,給自己一次學習機會,是我莫大的榮幸與補拙。尤其是看到很多創作者都站在自己作品前,眼睛亮亮地看著每一個駐足觀賞者與他們的評論,而我竟然也羞羞答答地變成這樣的“大師”。
站在自己的作品前,像有十五個吊桶打水,我總是七上八下地感到心里特別空虛,想起歌德的那句話:“只有在知道自己懂得甚少的時候,才說的上有了深知”。我就像是遇到“意外的情人”,而我的“意外”是指:在當今大小明星登場的時代,我既不想當名人的粉絲,也無意佔有不屬於我的那份頭銜,只因藝術大師廖天照的推薦與厚愛,一下子就把我推到了藝術的風口浪尖上,就像意外遇見情人般不知所措。
借用新北市市長朱立倫的話說:“文化能讓一座城市偉大,藝術則能充盈在地生活厚度”。換句話說,藝術是一種富有生命的東西,也是我們生活上的伴侶,不一定成為專家,但可以提供我們生活上的愉悅與詩意。在美學的散步中,我跟隨著藝術前輩優雅的腳步,在富含台灣精神與意象的作品中,讓我非常驚喜的看到,大陸廈門的“尋根”、山東的孔廟、桂林山水、屹立萬年的黃山奇石,像巨人一樣在松柏中昂首向天……特別是油畫作家李吉政先生,為了“尋根”的這幅畫,竟專程坐飛機回廈門——同安,尋找曾祖父渡海來台之前的痕跡,用濃重的油彩描繪出對岸“同安”老家郊區純樸的樹林、魚池及村婦,把思念之情用柔軟的畫筆融入故園的意境裡。畫中的風景和對家鄉祖國河山的萬種情懷,彷彿貼著我們的心,在畫幅的尺寸之間,遙接了萬代的情感。
繪畫與雕塑,是人類歷史最古老的藝術之一。尤其在原始社會,那些塗刻在山崖、洞壁、陶罐及廟宇上的動物人文,這些古老圖案,都表明了中華民族最古老最久遠的文明,就是通過繪畫與雕塑來體現的。而中國藝術家不僅用眼睛,更是用心靈之眼去繪畫,畫面中不管是遠眺雲山,近睹草木,煙煙云云,朝朝暮暮,盛盛衰衰。萬千景象齊匯於胸,怎不令你熱血沸騰呢!
竟然讓我想不到的是很多前來參觀的人對我的作品讚賞有加,從台北專程趕來的一個參觀團圍住我問這問那,突然使我忘掉了自己草根的身份,和他們友好地攀談起來:
“郭老師,我是林書豪的粉絲,您雕刻的太形象了,您也喜歡他嗎?”
“是啊,我是看到他為我們台灣爭光,所以才費了好多功夫,琢磨成了這件作品。”
“您這塊漂流木從哪裡弄來的?”
“是從花蓮的海邊。”
“適合這樣雕刻的漂流木很多嗎?”
“很少的,要在颱風過後去找,關鍵是材料難得啊!”
“是嘛?!郭老師,您真是一級棒,刻畫出了我們的最愛。”
他們要求和我合影,我站在這些民眾之間,一股自豪湧上心頭,渾身上下熱血沸騰,竟然忘了自己是個“濫竽充數”的傢伙。
有人說:“藝術就是修行”。因而這些年來,我盡量讓自己生活單純,遵循司馬中原老爺子的“人具有部分創造命運,掌握命運的權利”。在此方面,自覺有點叛逆的我,為不想讓生活的瑣碎黏住自己的翅膀,不想在物質偏頗裡養驕自己,總在無事裡面生點“非”,尋點“根”,即使吃再多苦,手臂一度累到五十肩(肩周炎)痛到抬不起來,也依舊擋不住我那點性靈展放的野心,總想在平地上做點想飛的夢……因為雕塑對於我,就像曠野的靈魂之舞,有些畫面看起來光影靜止,卻似乎有超乎旋律的東西在裡面燃燒,看了會讓人上癮,它能讓你忘卻塵念,活出具體的人生意義與自在。
夢在日子裡流動著,它就像世俗裡的一杯咖啡,它可以提神,也可以優雅,不管是吹捲成風,還是橫展成雲,夢卻一直在血液裡萌芽。尤其在台灣這塊豐厚的藝文特區裡,台灣師長與社會給了我太多的鼓勵與幫助,感覺自己被暖暖的人情包圍著。在此,我要特別感謝華人藝術家廖天照大師的感人相讓,感謝新北市政府主辦人丁寶華先生的支持與包容,讓我又一次汗顏的捧回一本精美的“新北市藝術家聯展”感謝狀。這些深放我心的生命貴人,我常常告訴自己,“不要忘了那雙扶起我們的手”。在寶島這塊藝文成長基地上,這些“意外地情人”和豐富的“濫竽充數”,我要懷著怎樣的謙卑與感恩呢!
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
一路走來 suyi 部落
http://suyiart.pixnet.net/blog
suyi 阿團 Go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suyiart
連絡方式:0937-054080 ( +886-2-24574310 )
豪華監獄裝灑脫 – 第五輯 燈下之絮語
豪華監獄裝灑脫 – 第五輯 燈下之絮語
那是一小段人生,是救急,也是救火。雖然已經過去很久了,但每當我走進廚房,就會想起囚犯般的72小時,困在億萬富翁的廚房裡假裝燒飯高手的窘迫。
我原在台北上班的那家公司,是一家專門介紹求職人員應聘家事的中介服務公司。主要工作是煮飯、打掃、照顧病人,或陪伴老人,或教小朋友英文,或接送小朋友上下學等等家事服務。
從事家事服務的人員來自大陸、台灣、越南、菲律賓等地,年齡從二十幾歲到五十幾歲。有專業看護,有廚師,有清潔工。工作時間8-24小時不等。這些應聘者報名之後,公司會按時組織週會,詳細培訓和講解服務理念、責任愛心,培養出一批批專業化的專職幫傭。
公司有一位億萬富翁雇主,長期指定我們公司的專職固定廚師,最近他的固定廚師回菲律賓了。雖然月薪高達六萬,但他要求每天“六菜一湯”變換花樣,因而公司派去的幾位幫傭他都不滿意。這天公司好不容易找到一位有煮飯經驗的小姐,卻不巧在上班的前一天病倒了。
公司的重點客戶,每天就是2000元啊!
熱鍋上的老闆不知怎麼就把獵奇的眼珠瞄上了我,他從來說話都硬邦邦的,現在卻軟的像小貓咪:
“郭小姐,我看只有你最合適了!”
“啊?我哪裡會做飯呀?老闆,你是在抬舉我吧?”
“真的啊!你做事認真,又會做大陸菜,你真是公司的救星呀!”
什麼公司的誠信呀,救火三天呀,施展抱負呀!我就這樣被他忽悠的找不到北了,匆匆拿了2本菜譜,就硬生生的從辦公室空降到億萬富翁的廚房,走進兩個截然不同的戰場。
第一天,推開雇主厚重的皮包大門,寬敞的客廳,巨大的窗戶投下炫目的光,一位八旬有餘的台灣企業家,靜靜坐在輪椅上,透過一副細框金邊眼鏡看向我,然後聲音啞啞沉沉地請我入座。旁邊一位長髮披肩,看似不到三十的長腿美女,像是一位陪伴主人的管家小姐,很溫柔地坐在主人輪椅旁邊的沙發上。我低著頭,只看到她細膩的手腳,白色指甲油發出清冷的寒光。她優雅略帶屈尊般地替主人問我:“你是哪裡的?會做菜嗎,你倒像一個女老闆呢!”
我心裡一慌,差點把包包掉在地上,但我馬上把心一橫:管她呢!她給老頭當管家,還不如我是公司職員呢,我怕她幹什麼?用不著自己嚇唬自己!於是我抬起頭來,很鎮定地微笑著說:“我不會西餐,不會日本料理,不會地中海風味的沙拉。”
她睜大了驚訝的眼睛,我立即補充上去:“一般的中國菜我都會做,比如麵條、包子、水餃、春捲、姑滓湯等,我都會做。”
我虎頭蛇尾自覺笑得很假,想要謙虛一下,可又忍住。因怕給公司露底,我就像被迫派出去的戰鬥士兵一樣,臨陣吃了豹子膽般不能疲軟。
“太好了!我們主人吃夠了菲律賓味的菜餚了!”
她起身帶領我走向廚房,還小聲告訴我,中餐晚餐主人、司機、護士、管家共四人吃飯,洗衣打掃衛生另有專人,我只負責煮飯。她特別囑咐我,中餐一定要隆重一點,晚餐可隨老主人的胃口,煮一點稀粥,弄幾盤素菜,搞定主人的胃就OK。
我還是兩眼直冒金星。
第一次站在別人家的廚房,看著現代化的烤箱、煎鍋、榨汁機、麵包機等電器我一竅不通,宛如旱鴨子上架無處下手。 “六菜一湯?”我立即清空了腦袋,想起台灣王小姐教我的油炸鱈魚,想起公司劉小姐教我的客家小炒,還有徐小姐教我的台式烤雞腿。我打開冰箱,將材料快速退冰,先醃雞腿,然後把鱈魚剔去中間魚骨,切成三分大小方塊,撒上鹽巴和胡椒粉。半小時後把青菜配齊,然後開始炸魚。我把魚塊滾上一層太白粉,倒好油用中火煎至薑黃。然後兩個烤箱火力全開,瓦斯爐上煮著食材,電動攪拌機快速轉動。我半小時看一次表,工作台上兩本翻開的食譜,一本沾有醬油,另一本沾著菜漬,我已顧不得廚房的整潔,只是血脈賁張慌手慌腳地直冒冷汗……天啊,烤箱為什麽會冒煙?慌亂中我趕快按下插頭,躡手躡腳探頭客廳。還好,偌大的客廳空無一人。我快速轉身從櫃子裡一堆清潔劑中,找到一瓶空氣清新劑,對著空氣狂噴一陣。這時已近午餐時間,我沒有時間分析,更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。當我手忙腳亂終於湊齊六個菜時,我的手已經被烤箱燙傷兩次,額角也被排煙機碰的生疼,看著端上去的菜品,腦袋已經一片漿糊。
他們竟然津津有味地吃起來,我在廚房里大念“阿彌陀佛”,感恩雇主大發慈悲,沒有把我立刻炒掉。到了晚餐,神經大條的我,只按老主人的胃口,熬了稀粥,弄點素菜,便蒙混過關了。
第二天,我動用意志力去拼六菜一湯,我打開冰箱,眼睛隨著思維,從黃瓜條跳到菠菜,再跳到竹筍、山藥,當眼睛跳到胡蘿蔔時,我突然一拍腦門,大腦立刻出現一個畫面:那是上個世紀60年代最貧窮的時候,我媽媽為了改善我們的生活,每個月都會用胡蘿蔔做一道“水晶大餐”餵養我們六個飢餓的靈魂。這道菜的做法非常簡單,就是把胡蘿蔔擦成絲,放一點鹽,放一點糖攪拌均勻後,再滾上一層麵粉,拌勻後上鍋蒸15分鐘。出鍋後粘在胡蘿蔔上的麵粉,經過濕氣蒸熟後,立刻變得透明紅潤,彷如水晶一樣叫人愛不釋手。尤其是在那個飢餓的歲月裡,吃一口就是過上了皇帝的日子。
而吃慣大魚大肉的有錢人,一定沒吃過這道菜。我立刻信心大增,馬上動手,在二十一世紀的廚房裡,做起二十世紀的水晶大餐,並自己安慰自己:今天只要有一個特色菜在桌上,其它的順其自然。當水晶大餐出鍋時,我還不忘精心選了一個精美的白盤子,除了紅潤的水晶飯外,我還切了幾片黃瓜片,用牙籤串成小花,萬紅之中一點綠,這樣紅白綠三大對比色,濃豔的猶如梵高的畫。我踮起腳尖,在50年之後的今天,端出了媽媽的“水晶大餐”。天啊,雇主也不知道我在廚房裡“搞什麼碗糕”(台語:指搞的什麼花樣),只見他早已期待地在腿上鋪上餐巾紙,喝著玻璃杯裡的氣泡水耐心地等待著。當菜上齊之後,我的眼睛便小鹿般忐忑不安地盯住了他們的眼球,那些油漬茄子、乾炸飛魚、五花肉燒海帶片像星星一樣拱著“水晶大餐”。還好,四雙筷子沒有在半空中停住,大家的臉上還蕩漾著飢渴,我幸運地混過了第二天。
第三天,走進偌大的廚房,看著發亮的工作台,我彷佛山窮水盡再也想不出什麼花招。我突然感到一陣恐慌,黑色的眼珠幾乎快掉出來了。我不知道下一刻能拿出什麼不一樣的菜系,但這是最後一天的戰場,我別無選擇。它讓我想起電影畫面,戰場上國軍軍官舉著手槍,叫士兵“給我頂住”似地不能抗命。我把頭貼在冰箱門上,挖空心思在想這十年來,我到底做過哪些比較檯面的飯菜……忽然,我想起十多年前在大陸廣州賓館喝的魚頭湯。那是我最喜歡的一道菜,是整個魚頭燉出來的奶白湯,就和牛奶一樣雪白滑嫩。我不知道廚師是用什麼配料燉出來的奶白湯,是大火燉出來的,還是倒了牛奶?我只能按我的
假想去做。好歹管家買回的魚頭很新鮮,不用醃,手掌般大的肥厚大頭,我直接破半給它下鍋,放進花椒、鹽與清水,再倒進一整瓶牛奶,然後扭開大火,下一步要怎樣我一點也不知道。正徬徨著,天啊,魚湯的泡沫洶湧地從鍋裡冒了出來,流到爐子上,又流到地上。我急忙關掉瓦斯,擦乾地面,看著只剩鍋底的一點魚湯,慌亂中我又加了一碗清水,為使魚湯濃稠,我又舀了兩大勺白色粉末,倒進鍋裡勾兌,然後擦擦頭上的汗,午餐時間還沒到,我早已累的雙腿發軟手心冒汗,氣血虛虧般不能自已。
過去我一直抱怨辦公室壓力太大,此時我人愣在那裡,感覺自己的靈魂遠離這座豪華監獄回到台北的辦公桌。到了晚上,當我全身冒泡般關掉最後一個洗碗按鈕,我終於肌肉疲軟地完成了為時三天的廚房大戰。感覺自己就像一隻所知有限的老鼠,一腳跌進這錯位的孤島,跌進一個錢味多於人味的深深庭院,人單形弱一人一國。那種高度的集中,和拿不出像樣的成績單之焦慮(特別是假冒的煮飯高手),感覺一點也不比真正的囚犯輕鬆多少。
當我一步跳出億萬富翁的大門時,彷彿走出“據點”,走出千山獨行的孤獨況味。望著台北的夜空,我深深地吸了一口自由之氣,雖然三天里水到渠成的6000之大鈔握在手裡,但卻一點也興奮不起來,公司老闆戲謔般第一句話就是“感覺如何?”我瞪了他一眼,千般滋味萬般無奈都已無法細說,我只能把它濃縮成7個字,以同樣別有意味的表情回敬他:“豪華監獄裝灑脫!”
人啊,真是沒有什麼不可以。
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日
一路走來 suyi 部落
http://suyiart.pixnet.net/blog
suyi 阿團 Go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suyiart
連絡方式:0937-054080 ( +886-2-24574310 )
在台灣 – 第五輯 燈下之絮語
在 台 灣 – 第五輯 燈下之絮語
在寫這篇文章時,我曾咬破一支筆桿,我穿著藍綠合縫的衣服,心裡總感到在滴血……
有一個小故事:“兩隻不同蟻群的螞蟻相遇,只是彼此碰了一下觸鬚,就向相反的方向爬去。爬了很久以後,他們突然感到遺憾,在這樣廣大的時空裡,體型如此微小的同類不期而遇,為什麼沒有擁抱一下?”同樣道理,以宇宙來看,微小如蟻的我們人類,在這個親密又疏離的藍色星球上,是什麼把我們堆湧在一起,又是什麼把我們殘忍地拆開呢?
特別是在台灣,幾百年的殖民、幾百年的移民、幾百年的歷史塵埃和幾十年的“藍綠”之分,在歷史脈絡複雜多元的演進聲中,衍生出的歷史恩怨,總在政治因素的變化下,一會兒澄清,一會兒渾濁。雖然近幾年已逐漸掙脫了對立的濃度,但每當地球公轉了四圈,選舉來臨之際,歷史悲情的藍綠對立、省籍刻痕、差異原罪等等,便會產生爆烈性的衝突,爆出歷史的舊痛與撕裂。恨不得把老祖宗從墳墓裡請出來,訴說歷史脈絡衍生的恩恩怨怨;恨不得涮清自己連帶的親情,把政治勢力的爭奪簡單歸咎於社會的舊痛與傷痕。即使是歷史冷飯,也有人誇大炒作,再端上桌來,雖然大家都是同胞,雖然差異不是背叛,故鄉也不是原罪……
回顧歷史,三國鼎立時期,東吳孫權就曾派軍隊出海遠征夷洲(公元230年),“夷洲”就是現在稱謂的台灣。
明朝末年,荷蘭趁明政府處境艱難之時,侵入台灣。不久,西班牙人也侵占了台灣北部和東部的一些地區,但於1642年被荷蘭人趕走,台灣淪為荷蘭的殖民地。荷蘭殖民者實行強制統治,把土地據為已有,強迫人民繳納各種租稅,把其收購到的中國生絲、糖和瓷器經台灣轉口運往各國,牟取高額利潤。 1662年2月,鄭成功進軍台灣,迫使荷蘭總督揆一簽字投降,台灣仍像以前一樣隸屬於福建省管轄。至1811年,台灣人口已達190萬,其中多數是來自福建、廣東的移民。
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,翌年清政府戰敗,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《馬關條約》,把台灣割讓給日本。從此,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達50年之久,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。
當我背對歷史、背對政治,一個人默默看海的時候,我就不明白,台灣的居民絕大多數都是大陸遷移過來的,而且屢遭外族統治,何以區分“大陸人” 、“台灣人”?
再後來,我聽到老一輩台灣人說,早期的台灣,因受日本教育餘毒很深,因而把國民黨遷台當成外來人,才衍生出今天的“本土”與“外來”。
二二八之後的五十多年,每個外省人身上彷彿都背上了一段沉重的往事。五十年前一群人哭,五十年後另一群人哭。老一輩一腳踏進這塊土地的外省人,他們早已落地生根把台灣當成了故鄉,含淚又揮汗地舖路架橋,出生入死,把青春和一輩子的血汗都撒在這裡的外省老伯們,他們該情何以堪?特別是在省籍情結最傾斜的2004陳水扁時代,真不明白他們何罪,為什麼要為歷史的恩怨埋單?
由於藍綠板塊的對立,遇到社會重大的議題,即使是立法院,也一樣因顏色的不同而爆吵、辱罵、撕扯、直至大打出手。會議現場常常是有人爭霸主席台,有人抗議舉牌,肢體語言一起來,常常吵成一團火焰。憤怒的一方眼球變色噴出藍色的火焰,嘶吼的一方皮膚變色泛出綠色的青光,再加上白色沸騰的口沫、亂掄亂揮的拳頭、以及突然飛來的一隻鞋子,會場頓時成了一幅畢加索的畫,顏色濃烈的化不開。
還有一些隱形的苦痛,使我想起上世紀美國發生的一個故事:一個在美國出生的中國人,長大以後卻留著辮子,美國人奇怪地問他:“為什麼偏要裝成中國人? ”他說:“我曾經剪過辮子,穿起西裝,說著流利的英語,然而我依然不能與你們混合,我感覺苦痛……”同樣的,在台灣也有許多人從美國回來,抱怨美國在一些認識的處理上,把台灣人當成二等公民。可是奇怪的是,就有一些人想不通2300萬生活在台灣的大眾都是同文同種的同胞,卻偏偏要在同胞中區分本土與外來,把同樣的苦痛強加給他人,挑起族群的對立。在這裡套用大陸作家余秋雨的說法:“人有多種活法,活著的文明等級也不盡相同,住在五層樓上的人完全不必去批評三層樓的低下,何況你是否在五層樓,還缺少科學的論證。”
在台灣,透過族群多元文化的網眼,還有一些隱而不顯的遺憾。比如藍綠朋友相處時,最好不要說“我是哪里人”,因為本地人會說“我是台灣人”,外省人會說“我是中國人”,不藍不綠的人會說: “我是中華民國人”等等。我們周圍有很多素養很好的人或家庭,他們有一千個理由可以成為好友或是相愛,但就因為不同的理念,如同碰了須的小螞蟻,彼此擦肩而過。一個行雲天空,一個流水在地,最終的結果都是浩瀚的海洋,但卻常常為了藍綠的“顏色”而捲起千堆雪。雖然大家都是中國人,可總有一條線在無形中區分著。其實,台灣幾十年的建設與發展,不但經濟實行了騰飛,還把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傳承的很好,許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,包括包容與愛在台灣比比皆是。台灣人的淳樸、台灣人的打拼、台灣人的忍辱負重,包括台灣人獻愛心、重捐助的奉獻精神,這些心目中最純潔的畫面,就像藍天下探向大海的椰子樹,顏色清新、氣味芬芳地在我眼前飄啊飄,搖啊搖,一直飄搖到很遠的思緒裡。
400年前的殖民地悲歌、一甲子的政治風雨、如今的藍綠紛爭,這一層又一層難解的歲月傷情,就像是暗流的土石流,沉澱在一個共同時代的命運裡,使每一個不同出身背景的人,都或福或禍地沉浮在其中。我就像禪院裡小和尚撒下的種子,隨風飄到了這個綠樹成蔭的寶島,使我有機會碰觸到不同社會、不同政治、不同的族群文化。每當我關起門來,聽著門外的風,就不知自己是讓眼睛習慣雜色,還是讓耳朵習慣雜音?
困惑,對家園的深厚擔憂,就像歲月裡無法打撈的陰影,在心底壓抑著。我常常捫心自問:當全球走向大同的今天,當人類已經征服了宇宙外空,當現代科技早已把世界鏈接成了一個村莊的時候,我們骨肉同胞心與心的鏈接,是天涯咫尺,還是只有一層窗戶紙?我們怎樣去彌補歷史的斷層,怎樣縮短和調和這些距離的危機呢?怎樣化解這些時代的痛點,和幾代人命運的痛點呢?
人生就是不斷變化的旅程,台灣是本省人的家,也是外省人的家,大家都關愛著這片曾經浸滿鮮血的土地,無論我們在哪裡落地,紮根久了就成了故鄉,誰也不能輕易就說轉身。
因為台灣的土地滲透的不只是文化,還有連骨帶肉的血淚和親情,割開了會痛,會流血,會悲哀,它早已隨歲月變成了我們生命的根,變成了我們揮之不去的家園與烙印。借用台灣知名作家劉墉的話說,就是:“我們因愛而生,因生而愛。我們用一輩子的時間,織這張生死愛恨的網,也用一輩子的時間,解那生死愛恨的結。只是,看穿了,生死愛恨能有多少距離?看破了,生死愛恨只是一念之間!”
摸索著寫下這些和我血脈相連的歲月感受,整整15年的紮根,終於看到兩岸盛況空前的商貿橄欖枝已高高豎起,渴望著明天會有一個自由的空間,讓兩岸的親情濃於這淺淺的海峽,讓沉浮的歷史塵埃還原出一個現實的公道,讓藍綠同胞交流的距離與紛爭自由宣洩社會的進步與開明。在此僅以自己一得之愚,借我儒弱的文字做一個小小蟻蟲般的嘆息!
天佑台灣!
二0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
一路走來 suyi 部落
http://suyiart.pixnet.net/blog
連絡方式:0937-054080 +886-2-24574310





.pn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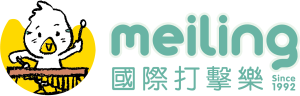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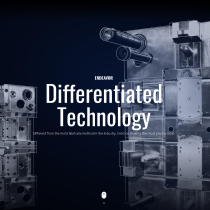
.png)


